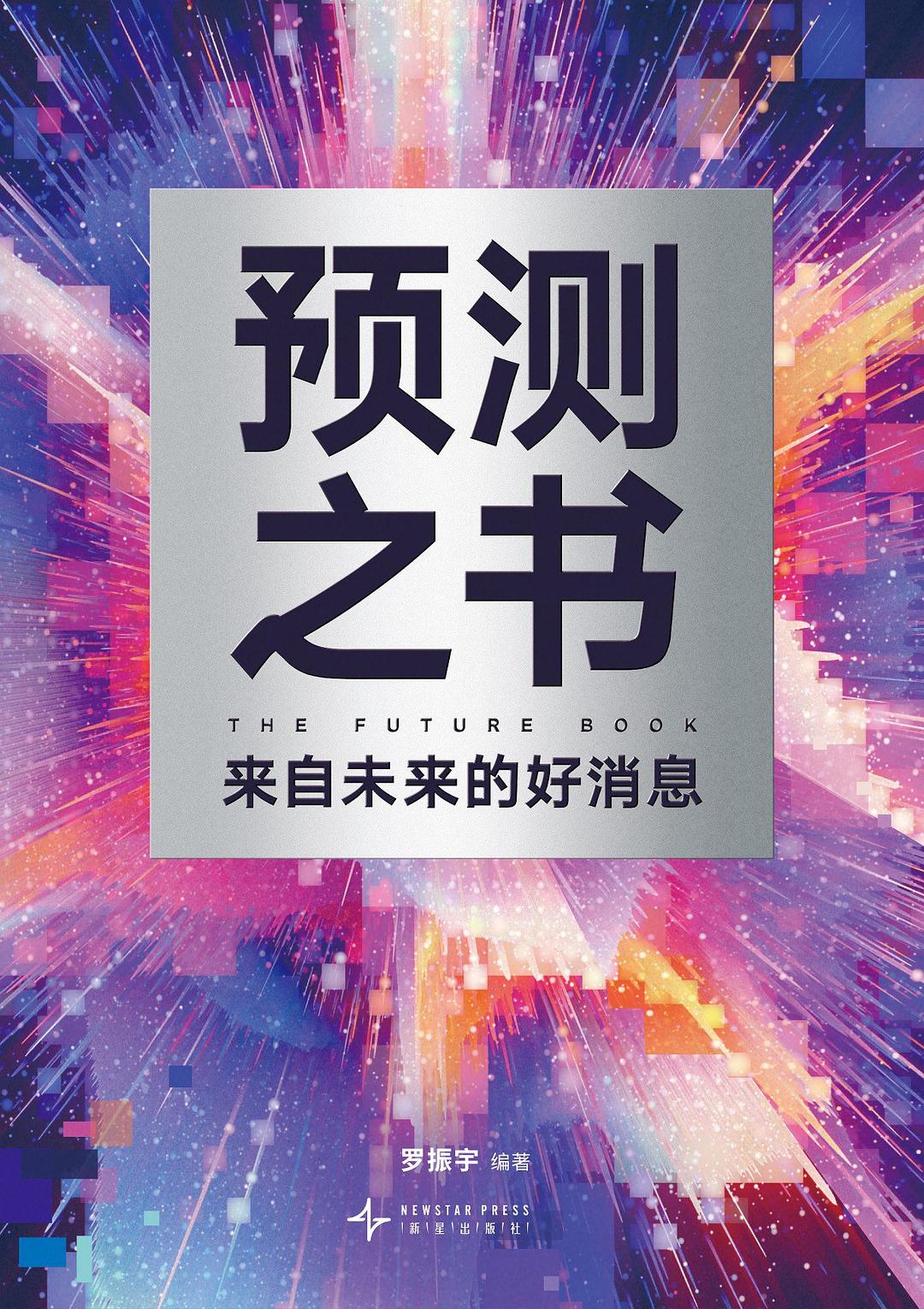AI的冲击,万物仿佛都是可以AI来完成。
然而,当越来越多的人意识到我们将命题权交给别人的时候,今天我们刚刚突破AI+的迷思时,明天又一个概念又会出现,而这个概念会让我们疲于奔命、疲于应对。为什么?潜在的因素在于“命题者”和“解题者”之间明显就是存在不平等,用别人的束缚来套用在自己身上。
焦虑,是因为不自知。真正需要什么?与其说眉毛胡子一把抓,不如来看看薛兆丰所分析的内容吧。
需求1:连接和从属的需求
虚拟陪伴已经应运而生,连接和从属的服务将会无远弗届,但人的孤独感恐怕不会消失,因为人还是想要更多。
需求2:好奇和求知的需求
未来的教育资源是充裕且廉价的,但教育水平的差距并不会因此消失。
不是书多了,博士就会多。 教育水平出现差距,主因不在于教育资源的可得性,而在于其他因素,如家庭环境、同学圈子、预期回报和持续训练等。 工作中用得上的知识是非常有限的,在学校里一下子就学完了。 学校应该发挥的是磨炼和贴标签的作用。 一般学校奉行的是快乐教育,而特殊学校奉行的是严苛教育。 不同的标签,是为市场里的雇主准备的。
需求3:对复杂体验的需求
过去,这些复杂体验是通过文字、音乐、戏剧和电影等单向的方式表达的,而未来,它们将更多地通过参与游戏的方式来获得。
游戏产业的发展将远远超过电影产业,因为前者为消费者提供了参与的机会。
需求4:对图像和故事的需求
未来教育普及的标准,除了听说读写以外,还会加上用图片和视频讲故事的基本要求。
需求5:对道德情操的需求
足够富裕的社会,人们出于慈悲可能会容忍各种“零元购”行为。随着物质生活条件的极大改善,加上在虚拟空间里志同道合者沟通成本的下降,原先牵引着道德标准的锚逐渐消失了,人们可选的道德标准开始更多地受到其他因素,如性别、基因、出身、宗教和党派等的影响。道德规范之争因此会变得愈发激烈。
需求6:从创作中获得满足的需求
种花、烹饪、唱歌、演奏、舞蹈、摄影、绘画、作曲……这些创作成为了大众的消费活动,人人都多才多艺。此时,大量的创作只能用于自娱自乐,在市场上可能供过于求了。
人们不忍心告诉专攻艺术的人,他们可能只是工匠,而非真正的艺术家。只有分清楚什么是基于个人兴趣的消遣,什么是为他人提供的服务,才能真正确认自己的职业定位。多才多艺的年轻人和艺术产品将会大量涌现,而对绝大多数人来说,专攻艺术很难挣到足够的钱维持生计。
需求7:对确定性的需求
人类对不确定性的恐惧是本性。技术的发展并不会让人类变得更理智,反而放大人类非理性行为的负面作用。换句话说,人是多目标的,发达的技术和丰裕的物质条件,使得人有资本纵容自己的非理性。AI系统的出现看似消除了很多不确定性,但是如果让不确定的东西少之又少,这是我们人类需要思考的事情。
需求8:对健康和舒适体感的需求
活得长不如活得好。恶性传染病、慢性疾病、保健免疫等医学研究。特别是病前预测和防范成为未来医学研究的重点。
从西医角度看,营养补充品、基因修正技术和饮食优化方案是否可以在婴幼儿阶段潜在的疾病干预。传感器是否能够安装在身体中,来预测、诊断和治疗?
另外一个就是睡觉。人要不要睡够8小时,睡得少就是活得长已经被商界人士所认同。如何提升睡眠质量和合理缩短睡眠时间,这是延长寿命的一个重要指标。
需求9:对人生意义的需求
Richard Dawkins在《自私的基因》中给出了生物意义上的回答:任何生命体都是基因为了不断自我复制而需要的工具。
从这个观点上看,生活本身没有必然意义。
但是,生活一旦加入了主体,即“我”,那技术每十年所产生的代际差异情形下,人性的表现方式将会丰富多彩,食物、居所、安全、知识、体验和确定性上的需求,推动了文明的极大发展。
那我的意义,就是要排除万难,不断进取。很多人愿意聆听和追随讲故事的人。正如,我们把我们的人生写成故事,讲给他人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