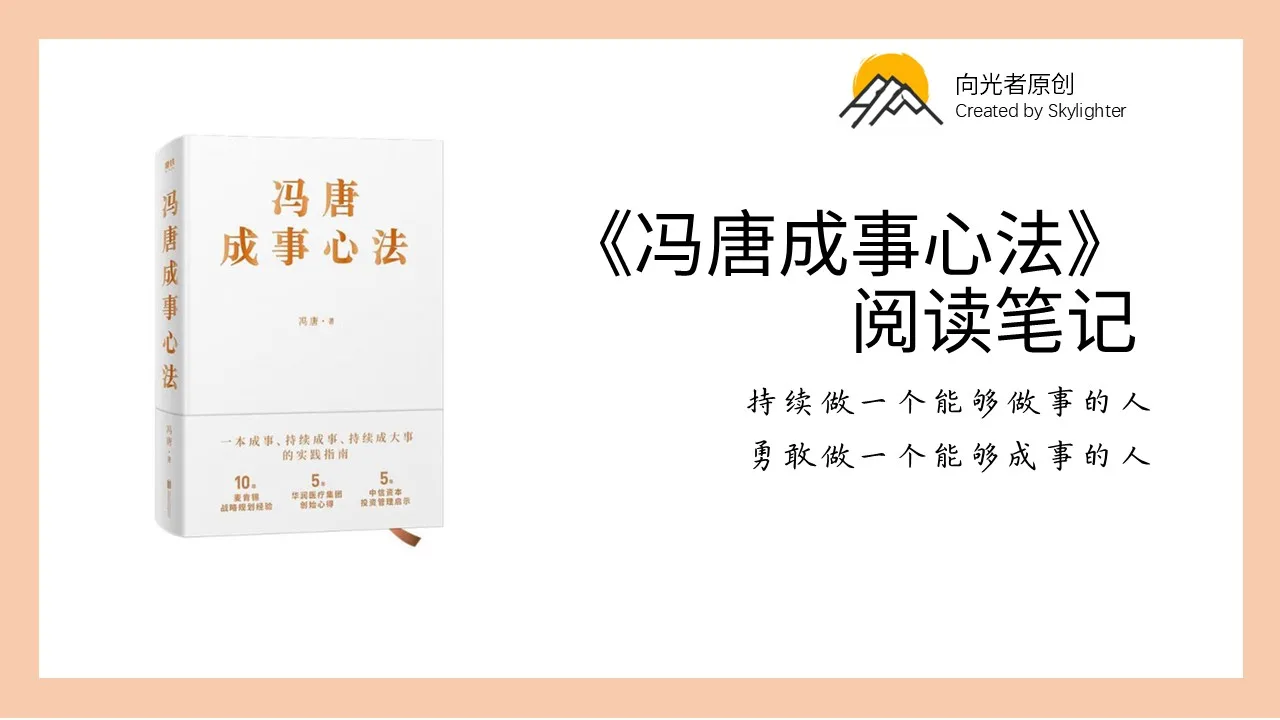从“要让孩子赢在起跑线上”到“30岁30人精英论坛”等等,整个社会对于成名趁早,成就要趁早的宣传可谓是无所不用其极。但是,鉴于整个社会的资源都集中在中老年人群手中,在学术界“杰青”、“优青”拿不上,意味着后续的机会大门就要关闭。在追求名、利的过程中,很多人容易迷失方向,最终走向自我毁灭的境地。
冯唐在本书中明确指出:学习只有先苦后甜,成名千万要晚,成大事无捷径,快乐学习是扯淡。
过早成名身体担不住
中国人有一种要出人头地,要争强好胜的心态。很多单位都是“开始就是冲刺”、“大干一百天”,甚至有什么“不是工作需要你,而是你需要工作”这样的话语,给人带来的思维就是:短跑、快冲、快进、拿第一。
我昨天和熟识的一个中医朋友聊天,他给我讲了一个故事:有一个985高校的硕士研究生来这里看病,四诊之后发现他二便有问题不说,还有失眠、焦虑感十足。和这个20多岁的小伙子沟通。小伙子压力很大:“我是从农村出来的,走到这里不容易,我一定要出人头地,给我父母、给我家人、给我们村争光。”这位中医朋友说:“如果你真的是天才,20多岁就不用读研究生了。能20多岁读研究生的人,就说明你就是一个普通人,先把自己照顾好再说。”
这个小伙子的故事成为了现在的缩影。我们这个社会容错性其实特别低,一步跟不上,步步跟不上。用一句话:“社会很无情,跟不上的就会直接被碾压在时代的车轮下方成为路基”。
至于那些端着的人,趁早成名了,很有可能不得不“端着”,为所谓的盛名所累。比如说35岁去世的女医生,面临“非升即走”的青椒们。
麦肯锡有一个“Up Or Out”——“上升或者出局”机制。能够升职的人不是看你总是拿第一,而是要看你能否实践出一些东西。
工作是场马拉松,有可能你要拿十年、二十年来看待,给自己一个学习、实践的过程。你以为懂了,很有可能你还没有真懂,让你迅速上位之后,你德不配位,你会被这个位子、被自己的名声累坏。
面对这个问题,冯唐给出了一个点:
脚步可以快,但是前提是要“稳”。请放稳脚步,一步一个脚印,慢慢往前走。
老老实实学习
凡事皆用困知勉行工夫,不可求名太骤,求效太捷也。困时切莫间断,熬过此关,便可少进。再进再困,再熬再奋,自有亨通精进之日。不特习字,凡事皆有极困极难之时,打得通的,便是好汉。
——曾国藩
做事,应该慢慢来做,努力来做,知道这件事情很难,一点一点去克服,不能求成名太早,也不能求出现效果太快。
昨天在学习革命家陈云同志的经历的时候,给我一个比较大的震撼就是他早就意识到,革命终会胜利,但是不是一蹴而就。做事情的时候,痛苦肯定要比快乐多,困境肯定会一个接一个来的。
我这两年的思考,越来越能够体会到我的一个启蒙师父所说“对于普通人来说,来是偶然走是必然,但是对于一个有修为的人而言,一个人来不是偶然,走不是必然”。来到世界上就是要你解决问题的。要不然你也不会平白无故来到这个世界上作为一个个体存在。当然,当你解决完所有问题的时候,自然而言要去换一种形态承担下一个任务。所以,不要偷懒,不要躺平。但行好事,莫问前程。
学习,就只有笨功夫。笨功夫,也就是真功夫。成名,别太看重,但行好事,莫问前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