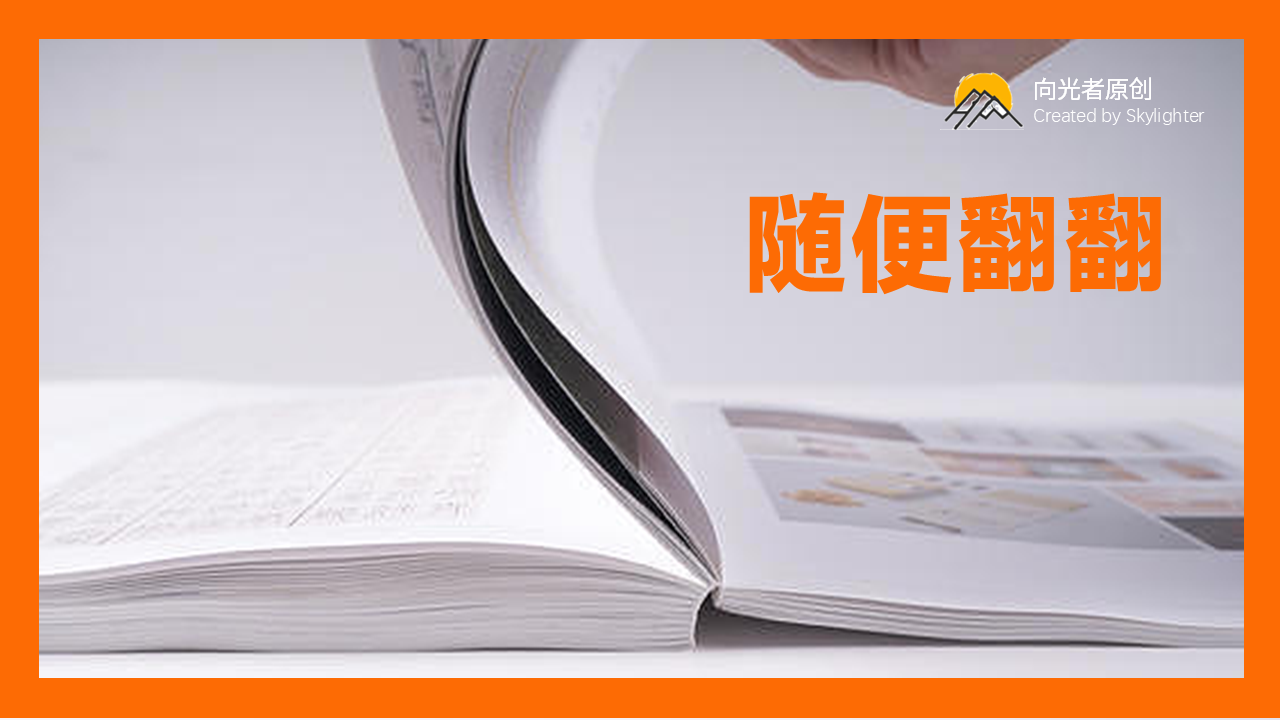清晨六点,我被心跳惊醒。那种熟悉的胸闷感又来了,像是有一块石头压在胸口,让我喘不过气来。窗外还是一片灰蒙蒙的天,楼下的早点摊子还没出摊,只有楼下那只流浪猫轻巧地跃上围墙,消失在晨雾中。
我已经很久没有真正睡过一个好觉了。白天工作时总是走神,脑子像被棉花塞住了一样迟钝;晚上躺下后却又异常清醒,翻来覆去想着那些没解决的问题,和那些让我筋疲力尽的关系。
有位作家写了一段话:一个人如果足够优秀、自律、专业能力出众,又待人接物得体,总让人忍不住想亲近。与他交往,仿佛每一次对话都能有所收获,每一段关系都带着温度。但很少有人知道,在这光鲜背后,藏着多少焦虑、抑郁与精神内耗。看完之后,深有同感,我虽然自认为不够优秀,但是在他人眼里还马马虎虎,所有人都愿意和我分享他们的人生故事,我很知足。然而,那种被掏空的感觉,就像手机只剩1%电量,却还要强撑着开机等待充电的机会。
最近,我的躯体化反应越来越严重——特别是肢体疼痛轮番上演,连最爱的精英日课也提不起兴致。我仿佛又回到了去年6月的自己,做什么都没劲,只想逃进一个无人打扰的角落。那时候,我甚至一度怀疑,是不是该去医院开点药,才能继续活下去。
不同的是,这一次我没有选择沉沦,而是学会了“自救”这个词。
第一个决定,就是断开那些把我当成情绪垃圾桶的关系。有一个朋友,他的本领很神奇。任何事情从他口中说出仿佛都能成为可以抱怨的事情。比如说学生们请他吃饭,他也要和我抱怨,然后征求意见。领导有一个公派出差的机会,明明已经结束了,但仍然会说两难境地。我印象中他会说“别人我没聊的,只能祸祸你”。而我,每次都要像个心理医生一样听他倾诉,安慰他、鼓励他,可他每次开头总是会问“你现在有事吗?”而不会去问过我一句:“你最近还好吗?”这种自杀式的社交,我是真的做不到。
断连是在一个周日晚上。我写了个草稿,然后用大模型略微润了个色,发完那条信息后,手都在抖。但我没想到的是,这哥们直接把我的消息放到大模型里,然后让它直接生成回复模板,复制,转发过来。这倒让我看透了一个人的心境。第二天醒来,心头仿佛卸下了一块巨石,整个人轻松了许多。那一刻我忽然明白:“凡墙皆是门”,堵住的路,也许正是通往自由的出口。
人生的前半程,我已经经历了四五次重大的转折。从大学毕业后独自北漂,到辞职转行读研、读博;从经历丧妻之痛到公权力部门的不公待遇,到学会独处和自愈。在这个阶段,凭借回忆去写一些旧事,难免会有错漏,所以我想,与其评判他人,不如只谈自己。
最近读书时看到一句话给我特别大的启发:“世界上只有两种事情,一种是‘与我何干?’,一种是‘与你何干?’”这句话像一记清脆的钟声,敲醒了我混沌的心。
前几天,得知香港著名作家蔡澜离世。回顾他的人生,我发现人这一辈子至少得居住生活过5个城市,才能够知道哪里才是让自己心安的地方。我在北京长大,在上海工作,在成都旅居过一段时间,如今在广州定居。每个城市都留下了一段故事,也塑造了现在的我。
我喜欢在雨后的古城里散步,喜欢老的集贸市场里看人来人往。我喜欢结交有趣的人,体验有趣的事,和他们成为朋友。大千世界还有那么多我没有探索和经历的风景,何必困在一段段消耗我的关系里?
于是,我给自己定下一个原则:“若愿彼此相伴成长,我愿倾尽所能;若只是抱怨吐槽无休,三次即止,不再纠缠。”
世间之苦,不彼此加油打气,而只单方面索取的友情不值得珍惜。毕竟就这几十年光阴。
拒绝,很难。但把一个人逼到墙角,怕是再小心翼翼的人,都不会丧失自我,把最后的一点领土割让出去,反而会迸发出反抗的力量。所以,一旦遇到事情,自救吧。
抑郁症见鬼去吧。
此刻,阳光终于穿透云层洒进窗台,坐在工位上,泡好的茉莉花茶静静地摆在桌上,打开word和Visual Studio,准备开始一天的工作。我知道,这只是新的开始。
许美静的声音回响耳畔:阳光总在风雨后,乌云后有晴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