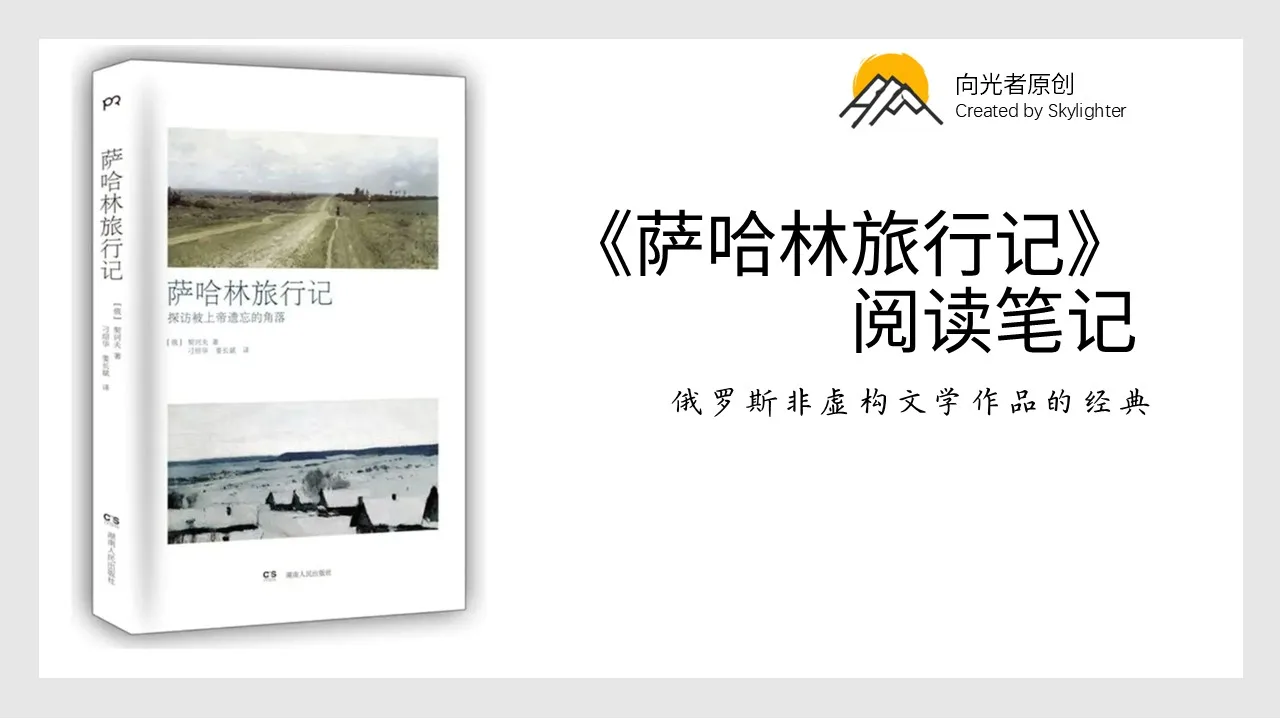为什么要流放犯人?
其⼀是净化社会,转移底层⻛险,通过把脱序者,也就是背离主流社会规则的⼈,丢到荒僻的远⽅,让核⼼地区社会⽣活回归常轨。
其⼆是清除政治威胁,消灭反对声⾳。流放⼗⼆⽉党⼈、⺠粹派、布尔什维克分⼦,乃⾄⼀般的知识分⼦,就是这个⽬的。
其三是获取奴⼯,⽤于殖⺠开发,充实边陲。
其四是制造社会恐惧。
这让我突然想到了一个很敏感的词汇,也就是将清理低端人口。而这些低端人口一旦到了萨哈林,过的日子其实比本地人还要凄惨。更让人发现的是,当人们开始对此麻木的时候,不正常反而成为了常态。能放到萨哈林的人,大多数因为打架斗殴、击毙人命,被判终身监禁甚至死缓的。
不正常的“混日子”
萨哈林,当你近距离接触,会发现这里存在着好多人。
最高档次的,生活哲学就是“混日子”:大多数被流放在这里的苦役犯可以满大街转,手里拿着斧头、锯子和锤子,维持着岛上基本生产。例如挖煤、淘金、刨树、建房、疏浚沼泽、捕鱼、割草、装卸轮船等等。女苦役可以作为保姆。例如,一个摆渡工,衣衫褴褛却自得其乐:你只要服从,麻痹自己,生活就不错。苦役犯和流放农⺠开荒种地,撒下种⼦,结果只能收获两三倍种⼦
的收成。这样的农业简直是笑话。在煤矿⼲活的苦役犯们也被迫⽣产但是产出甚微。甚⾄就连捕捞⼤⻢哈⻥这样的简单⼯作,在萨哈林也做不好,为了图省事,⼈们只在上游捕捞半死不活的⻥,结果煮出的⻥汤都是臭的。
看似很正常吧,思想感觉更是正常。
然而,当你走进牲畜,就发现有问题了。狗都拴着绳⼦,猪脖⼦上拴着⽊枷,连公鸡都拴着腿。
有没有感觉一首歌浮现在脑海里。写到这里,我打开了音乐播放软件,边听编写。
当奴隶才有活路?
在萨哈林只有两种人能够有活路:乐于施虐者与麻木被虐者。前者是小特权阶级,后者则是奴隶。
谁都知道:奴⾪没有⽣产⼒,⾃由⼈才有⽣产⼒。然而,有一种体制就能够把⼈变成奴⾪,扼杀其⽣机,他们就会成为废⼈。
在本地,赚钱只能靠⾮法的⼿段,倒卖犯⼈的物品、盘剥异族⼈、私卖烧酒、放⾼利贷、赌博,等等。
岛上的赌博相当疯狂,⾼利贷者也⼗分残忍,索取10%的⽇息,甚⾄借⼀⼩时也要10%的利息。抵押物品⼀天之内⽆⼒赎回,就归⾼利贷者所有。卖淫普遍到⼏乎涉及所有⼥性的地步。⾃由农⺠⼥性,甚⾄相对上层的⼥性,也⼀样。为了去杜厄和沃耶沃达监狱向囚犯们出卖⾁体,⼥苦役犯和⾃由妇⼥踩出了⼀条⼩道。她们这么做只能得到⼏个铜板,可是如果不卖淫,这⼏个铜板也得不到。
契诃夫说,需求量⼤,卖淫的⼥性年⽼⾊衰,或相貌丑陋,甚⾄三期梅毒,都⽆妨碍。年纪幼⼩也⽆所谓。
如果上面说了,奴隶是这样,那么特权阶级呢?
一个军医助理,平时最大的乐趣就是看行刑:为了看到了残忍的场面而洋洋自得。
想到这里,我突然想到了之前有一个貌似富二代的人,一边抽打一个自称警花的年轻女士,骂她是狗,是畜生,还让她摆出各种扭曲的姿势发泄这个富二代的淫欲。而这个女士却乐在其中。是她麻木了吗?我不知道。
但是,在我们的世界中,到底有多少人愿意为了一些微不足道的钱而去出卖作为人本身的尊严?唉,人吃人的社会啊。
萨哈林是传奇吗?当然不是,萨哈林的代名词是恶的麻⽊和麻⽊的恶。恶与麻⽊,互为表⾥。这是⼀种⼀切都⽆所谓,⽆所谓明天,也⽆所谓过去,⽆所谓道德,也⽆所谓⼈性的麻⽊。
看守像念经⼀样数着数字,⾏刑员挥舞着鞭⼦,被鞭打的犯⼈最初⾯⽆表情,然后全身痉挛,脖颈涨得⽼粗,开始嘶叫和哭泣,再下⼀步是求饶,随着鞭打的持续,犯⼈进⼊了醉酒似的状态,数落⾃⼰,⼜伸⻓脖⼦,发出呕吐的声⾳,⽽鞭打似乎永⽆休⽌。
另外一种畜生
当自由被剥夺,要么反抗,要么麻木。
恶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