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看清“制度之墙”,就要明白:不要把社会的善,寄托在个人的道德上。再好的人,若制度鼓励恶,他也难独善其身;再普通的人,若制度奖励善,他也会选择向光而行。真正的文明,不是歌颂个别清官,而是建立让所有官员都不敢贪、不能贪的机制。
今日小故事
《资治通鉴》记载,唐代名臣魏征以“敢谏”著称,屡次当廷驳斥唐太宗。太宗曾怒极欲杀之,长孙皇后却着礼服庆贺:“君明则臣直,今有直臣,正见君明。”魏征死后,太宗亲题碑文:“以铜为镜,可正衣冠;以史为镜,可知兴替;以人为镜,可明得失。”然而,魏征若生在另一朝代,结局可能截然不同。
明嘉靖年间,御史杨继盛弹劾权相严嵩,言辞激烈,最终被构陷入狱,惨死狱中。同为言官,一生成一代名臣,一生命丧黄泉。差别不在个人勇气,而在——制度是否真正赋予监督者独立性与安全保障。当监察者可被权力轻易“搞定”,所谓“制约”便形同虚设。历史一再证明:好人能否行善,不取决于他有多高尚,而取决于制度是否允许他不沉默。
哲理
制度托底
人性本有善端,如孟子言“恻隐之心,人皆有之”;亦有私欲,如荀子谓“生而有好利焉”。一个社会能否向善,关键不在期待人人成圣,而在制度能否抑制恶的释放,激励善的表达。若升迁只取决于上司喜好,而非公众福祉,则下属必投其所好,谄媚、造假、打压异己等“黑暗技能”便成生存必需。此时,不是人性变坏,而是制度奖励了坏的行为。正如经济学中的“激励相容”原则:人会朝着收益最大化的方向行动。若作恶成本低、收益高,再有修养的人,也难持久抵抗。
监督
御史台、言官、监察院……历代皆设监督机构,但若其任免、考核、安危皆系于被监督者之手,则监督必失效。历史反复上演同一剧本:权臣掌权后,先控言路,再除异己,终至“万马齐喑”。真正有效的制约,必须来自独立于权力体系之外的力量:或是法治的刚性程序,或是多元的舆论监督,或是分权制衡的结构。否则,“自我修养”只是奢侈品,多数人只能在“同流合污”与“自我毁灭”间抉择。制度的意义,正是要减少这种残酷选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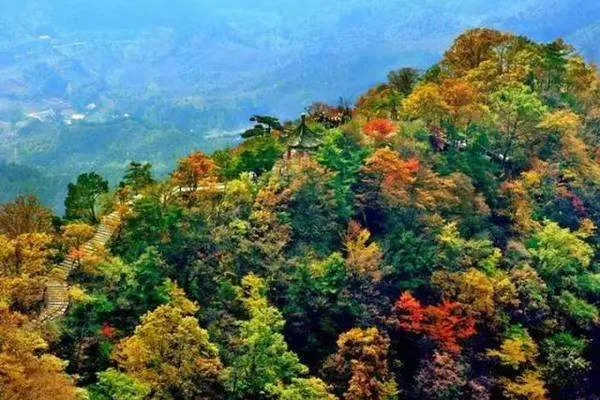
人性如水,制度是渠;
王勇先生
水可载舟,亦可覆舟,
关键在于渠是否坚固,流向是否清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