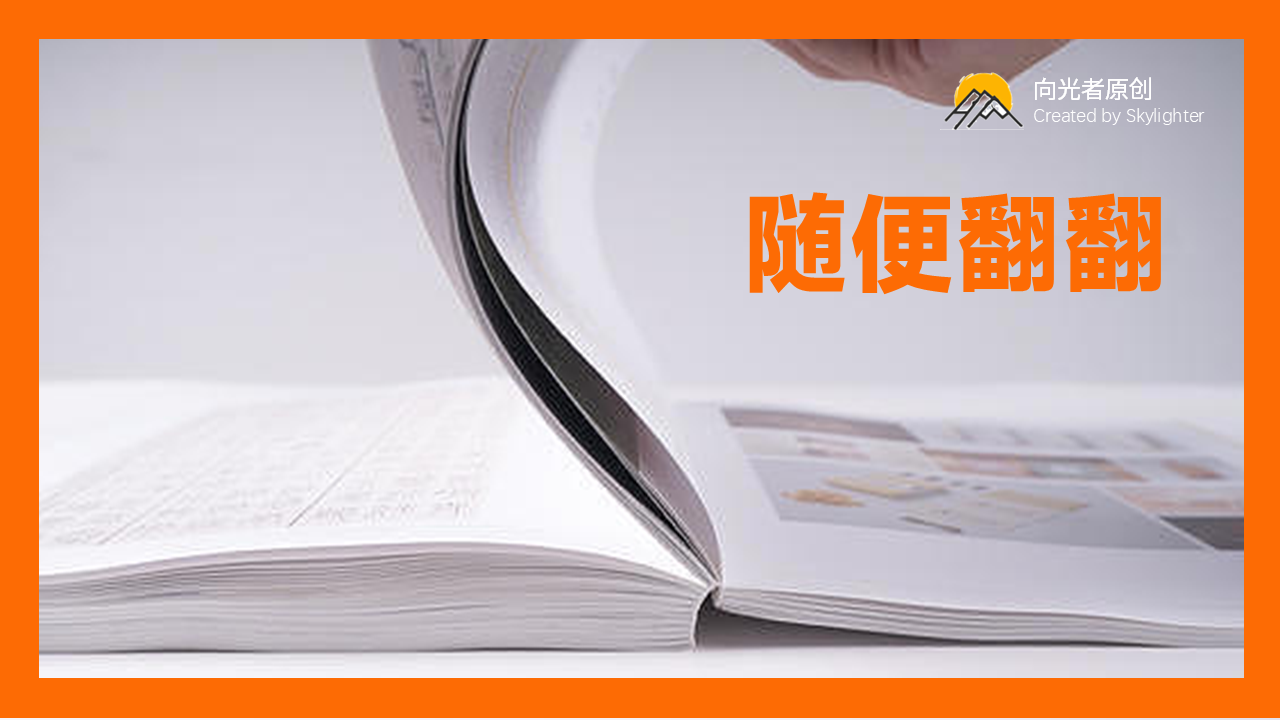罗密欧和朱丽叶可谓是中国中产阶级及以上人士所熟知的爱情悲剧。它是由1597年莎士比亚的戏剧《罗密欧与朱丽叶》首次呈现。讲述了蒙太古之子罗密欧与凯普莱特之女朱丽叶,在家族世仇背景下的爱情悲剧。上演的歌剧包括了两首开场诗和五幕二十四场组成。
在莎士比亚写下“这是一个多么光明的世界,却容不下一对恋人”的瞬间,罗密欧与朱丽叶的爱情便不再属于16世纪的维罗纳,而成为穿越时空的情感原型。四百余年来,这个关于宿命、激情与死亡的故事,被无数艺术家反复重述——尤其在音乐领域,它催生了超过千部作品,从挽歌到交响诗,从芭蕾到音乐剧,每一次旋律的响起,都是一次对“爱何以可能”的追问。
而今回望,《罗密欧与朱丽叶》的音乐接受史,不仅是一部艺术风格的演变录,更是一面映照时代精神的镜子:它从古典悲剧走向现代反思,从男性视角转向女性觉醒,从宿命论调迈向个体救赎。
实际上早在这个戏剧出现之前,这个故事的版本就很多了。莎士比亚主要参考的是亚瑟·布鲁斯(Arthur Brooke)1562年的长诗《罗密欧与朱丽叶的悲剧史》,此诗译自班戴洛的故事。不过还有原型追溯到这几个:
- 奥维德《变形记》中的《皮拉摩斯与提斯柏》:两个巴比伦青年因家族反对而秘密相恋,最终双双误会导致自杀。这一“墙缝传情”、“误信死讯”、“殉情结局”的结构,几乎就是莎剧的蓝本。
- 色诺芬《阿伯柔科斯与安提亚》(可能指《以弗所少女》):虽非完全对应,但“恋人分离—生死考验—重逢救赎”的模式也影响了后世爱情叙事。
- 马苏乔·萨勒尼塔诺(15世纪意大利作家):其《故事集》(Il Novellino)中已有类似情节雏形,后经班戴洛(Matteo Bandello)等文艺复兴作家改编,最终成为莎士比亚的直接灵感来源之一。
在1991年出版的《莎士比亚音乐作品目录》中,关于罗密欧与朱丽叶相关的音乐作品高达1130个。从十八世纪到今天为止,不同阶段对于这部经典的音乐诠释截然不同。
18世纪:挽歌、歌剧与芭蕾音乐
挽歌起源于英国,形式简单、篇幅短小,属于纪念逝者的葬礼音乐。目前所知,以罗密欧与朱丽叶为主题的音乐作品最早出现在1750年,分别是托马斯·阿恩的《庄严挽歌》和威廉·博伊斯的《为罗密欧与朱丽叶而作的挽歌》,以简练和声表达哀思,反映当时英国教堂音乐传统的影响。
1776年,波西米亚作曲家格奥尔格·本达索创作的三幕歌剧《罗密欧与朱丽叶》是现存最早的以罗密欧与朱丽叶为题材的格局。与莎士比亚的创作不同,在创作这个歌剧时,通过删减辅助角色,并将结局改为了有情人终成眷属的喜剧,凸显这个与众不同。
芭蕾音乐包括洛伦佐·拜尼,路易吉·马雷斯卡尔奇等人创作的,但多为片段式舞曲,未形成完整叙事芭蕾。
19世纪:交响乐、艺术歌曲与钢琴音乐
交响化、歌曲化和钢琴化成为了19世纪西方音乐创作的特点。对罗密欧与朱丽叶的创作达到了高峰。
比如1839年艾克托尔·柏辽兹的戏剧交响曲《罗密欧与朱丽叶》,就是人声和器乐相结合的交响戏剧,器乐在场景描绘、角色刻画和情感表现上发挥了巨大作用,人声则以旁白的形式穿插于各乐章间来描述内容。此外,第六乐章的“墓地”进行了改编,体现了柏辽兹天马行空的想象。1867年古诺的同名歌剧尊崇原典,是音乐史上以歌剧再现莎士比亚戏剧的经典之作。
柴可夫斯基的管弦乐序曲,则是将原著浓缩为单乐章的纯器乐作品,提炼出戏剧的核心主题——世仇、爱情与和解,创作了械斗主题和爱情主题,有意奏鸣曲式表现矛盾的对立与统一。它捕捉了推动戏剧发展的“劳伦斯神父”,并创作了神父主题。引子劳伦斯神父主题(低音弦乐庄严缓慢),呈示部:蒙太古与凯普莱特械斗主题(激烈铜管与打击乐),副部:朱丽叶爱情主题(双簧管奏出如歌旋律),展开部:命运压迫与悲剧推进,再现部:爱情主题变形,终归沉寂,被誉为“最莎士比亚式的音乐”,至今仍是音乐会常演曲目。
此外,马斯内的管弦乐组曲等等也值得一听。。
艺术歌曲的发展和钢琴的普及,使得钢琴作品踏足了《罗密欧与朱丽叶》。例如理查德·辛普森的《当悲伤萦绕在心间》,奥多阿多的《晚安,parting is such a sweet sadness》。卡尔·本德尔的《麦布仙后的华尔兹》,威廉·斯莫伍德的《朱丽叶》以及西里尔·卡尔顿的独奏加沃特(一个曲种)《朱丽叶》等。
20世纪:震荡
歌剧、芭蕾、交响乐、歌曲和钢琴作品已经成为了这个世纪的主流创作重心。例如普罗科菲耶夫的芭蕾舞剧、管弦乐组曲和钢琴组曲《罗密欧与朱丽叶》。
另一方面,受到表演艺术“本真演奏”和“古乐复兴”的影响,又有很多古老的乐器和体裁被融入到了其中。
典型的是1960年詹姆斯·福特在《莎士比亚戏剧<罗密欧与朱丽叶>的前奏曲》就运用了低音维奥尔琴。
哈里·弗里德曼在芭蕾音乐《星际恋人》中使用了文艺复兴古乐团。
赫尔穆特·韦斯与约翰加德纳分别于1956年和1964年创作了康塔塔。
后面有些人过度强调世仇、还有帮派之间的斗争以及政治纷争,这个就不再说了。
21世纪:个性化诠释
真正颠覆性的转变发生在21世纪。新一代艺术家不再满足于复述悲剧,而是提出一个大胆问题:如果朱丽叶没有死,她会怎样?
音乐剧:2000年捷哈·皮斯葛维克创作的法语音乐剧作为开篇。2007年,里卡多·库夏特作曲的同名意大利语音乐剧。2019年,瑞典流行音乐教父马克斯·马丁创作的音乐剧《朱丽叶》提出了“如果朱丽叶没有自杀”的疑问,然后朱丽叶发现罗密欧死后,奔赴巴黎,在派对中又找到了新的爱情,从而表达了自我救赎和独立女性的形象。音乐融合流行、电子、摇滚,体现当代青年文化。
芭蕾舞剧:2005年,罗马尼亚爱德华·克拉格《广播与朱丽叶》,以朱丽叶从墓地中苏醒为开场,以她的回忆勾连每个戏剧场景,这显得非常的简洁和另类。“广播”元素暗示媒体对爱情的建构与扭曲,是典型的后现代解构手法。
国内发展
当然,身处广东,我的粤语伙伴也告诉我,在香港,亦舒的广播剧《现代罗密欧与朱丽叶》将家族世仇转化为都市阶层差异,用粤语的细腻语调讲述当代青年的情感困境;在内地,田沁鑫导演的话剧《罗密欧与朱丽叶》(2014)融入《栀子花开》等流行歌曲与爵士元素,使古典悲剧落地为都市哲思剧场。这些改编虽未完全颠覆原作结构,却已悄然将“爱情与社会压力”的议题植入本土经验。
- 2023年上海芭蕾舞团推出《简·朱丽叶》,将朱丽叶塑造成独立舞者,脱离罗密欧存在
- 中央音乐学院曾改编柴可夫斯基序曲为民族管弦乐版,加入古筝与箫
更值得期待的是未来中国艺术家能否进一步提出属于我们时代的“如果”——如果朱丽叶生在今天的中国,她会选择逃离家族,还是挑战体制?她的爱情,是否还能成为改变世界的起点?
永恒主题的永恒回响
《罗密欧与朱丽叶》之所以历久弥新,并非因其情节多么曲折,而在于它提供了一个永恒的命题:当个体情感遭遇结构性压迫时,我们该如何自处?
从18世纪的挽歌到21世纪的流行音乐剧,从柴可夫斯基的命运交响到马克斯·马丁的电子节拍,每一次音乐的重述,都是一个时代对这个问题的回答。
曾经,我们赞美“生不同衾死同穴”的忠贞;如今,我们更愿看见“生而独立,爱亦自由”的可能。从殉情到觉醒,从悲剧到重生,《罗密欧与朱丽叶》的音乐变奏,正是人类情感文明不断演进的见证。
或许终有一天,我们会迎来一部真正的《朱丽叶独白》——没有罗密欧,没有死亡,只有一个女人,在阳光下说出她的名字,和她想要的生活。
那才是爱情最明亮的胜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