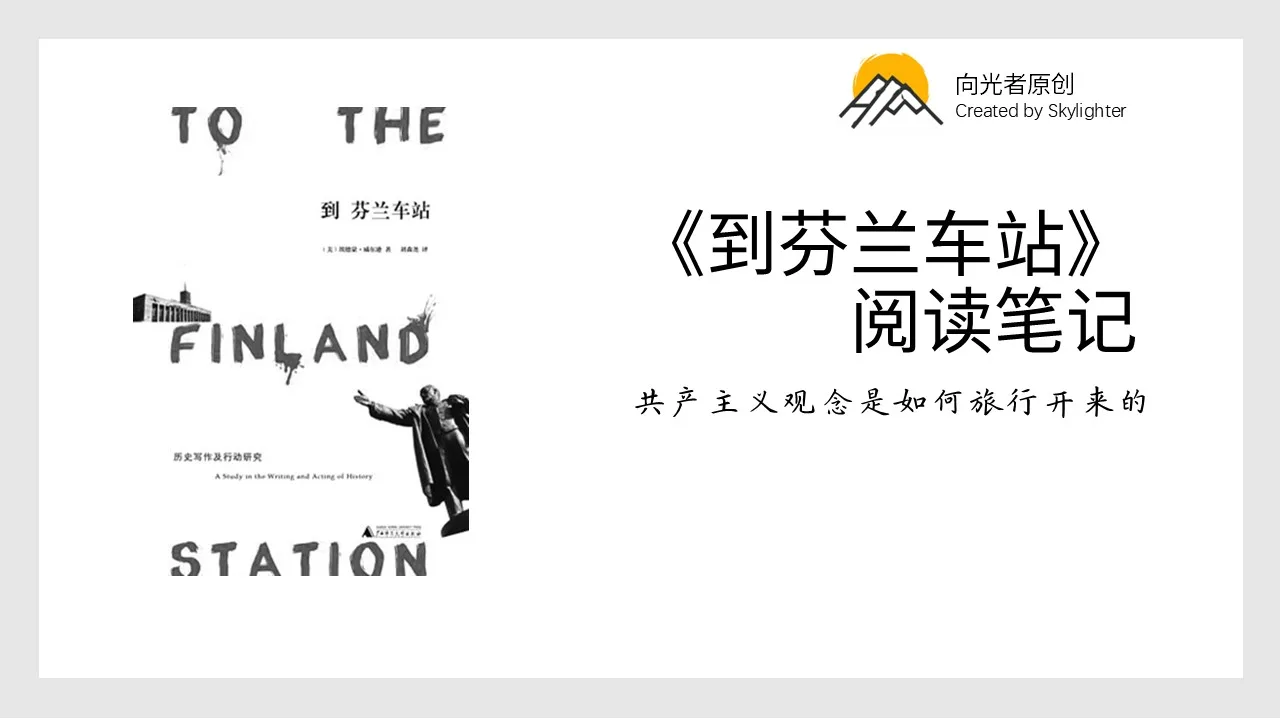马克思留给后世最振聋发聩的一句话,莫过于:“为人类工作。”这不仅是一种理想,更是一种行动的召唤。而《共产党宣言》正是这一召唤在历史中的第一次系统回响。
从共产党宣言中看问题
这是共产党宣言的一段话:
资产阶级在它已经取得了统治的地⽅把⼀切封建的、宗法的和⽥园诗般的关系都破坏了。它⽆情地斩断了把⼈们束缚于天然尊⻓的形形⾊⾊的封建羁绊,它使⼈和⼈之间除了⾚裸裸的利害关系,除了冷酷⽆情的现⾦交易,就再也没有任何别的联系了。它把宗教的虔诚、骑⼠的热忱、⼩市⺠的伤感这些情感的神圣激发,淹没在利⼰主义打算的冰⽕之中。它把⼈的尊严变成了交换价值,⽤⼀种没有良⼼的贸易⾃由代替了⽆数特许的和⾃⼒挣得的⾃由。总⽽⾔之,它⽤公开的、⽆耻的、直接的、露⻣的剥削代替了由宗教幻想和政治幻想掩盖着的剥削。
这段文字穿越一百七十余年,依然如一面镜子,映照出当代社会的某些现实切片:
个别外贸从业者,打着“自由贸易”的旗号,实则以无底线的逐利逻辑,侵蚀着诚信、责任与行业伦理——这不正是“没有良心的贸易自由”的当代写照?
在一些客家聚居区,人们仍保留着宗族伦理、邻里互助与乡土温情——那是尚未被资本逻辑彻底冲刷的“田园诗般的关系”;
而在江浙等高度市场化的地区,人际关系日益被简化为交易与算计,温情脉脉的面纱几近消散;
东北某些地方,昔日“小市民的伤感”如今化作抖音直播间里的表演与打赏,人的尊严被悄然编码为流量与收益;
……
《宣言》所揭示的,不仅是19世纪欧洲的现实,更是资本逻辑在全球扩张过程中不断重演的结构性命运。
而当历史行进到20世纪初,列宁的出现,则为这一命运提供了另一种可能的回应。
1917年1月,流亡瑞士的列宁尚在日记中写道:“恐怕没机会活着看到革命的殊死战。”然而仅仅两个月后,二月革命爆发,沙皇退位。消息传来,他立刻意识到:历史的闸门正在开启。他坚持“搭下一班火车立刻出发”,不顾一切返回俄国——这不是莽撞,而是一位革命者对“历史时机”的精准把握。正如他后来所言:“有时候,几十年什么都没发生;有时候,几周就改变了整个世界。”1917年4月,正是这样的几周。
更富戏剧性的是,列宁一行借道德国回国。彼时德国是俄国在一战中的敌国,此举被政敌斥为“通敌”。但列宁清楚:革命高于战争。德国人希望他搅乱俄国后方,列宁则反过来利用敌人的算计,为社会主义革命开辟道路。这并非道德妥协,而是在极端条件下,以现实主义策略服务于更高理想的政治智慧。
当他站在彼得格勒芬兰车站的装甲车上,探照灯照亮红旗,群众自发涌来——这一幕成为革命美学的经典意象:黑暗中的光,冰冷铁甲上的热血,旧秩序崩塌的轰鸣与新世界诞生的胎动在此交汇。列宁的归来,不是英雄凯旋,而是火种传递。他带着十四年流放的疲惫与愤怒,却以不可阻挡之势,冲进了历史的风暴中心。
从《共产党宣言》对资本异化的深刻批判,到列宁在历史关头的果敢行动,我们看到的不仅是理论与实践的结合,更是一种“为人类工作”的信念如何在现实的泥泞中扎根、生长、爆发。
今天重读这些文字与历史,并非为了怀旧,而是为了追问:在资本逻辑依然主导全球秩序的当下,我们是否还能辨认出那些“田园诗般的关系”所承载的人性温度?是否还能在“现金交易”之外,重建人与人之间基于尊严、互助与共同命运的联结?是否还能像列宁那样,在看似无望的时刻,依然相信“几周就能改变世界”?
或许,这正是马克思那句“为人类工作”留给我们的永恒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