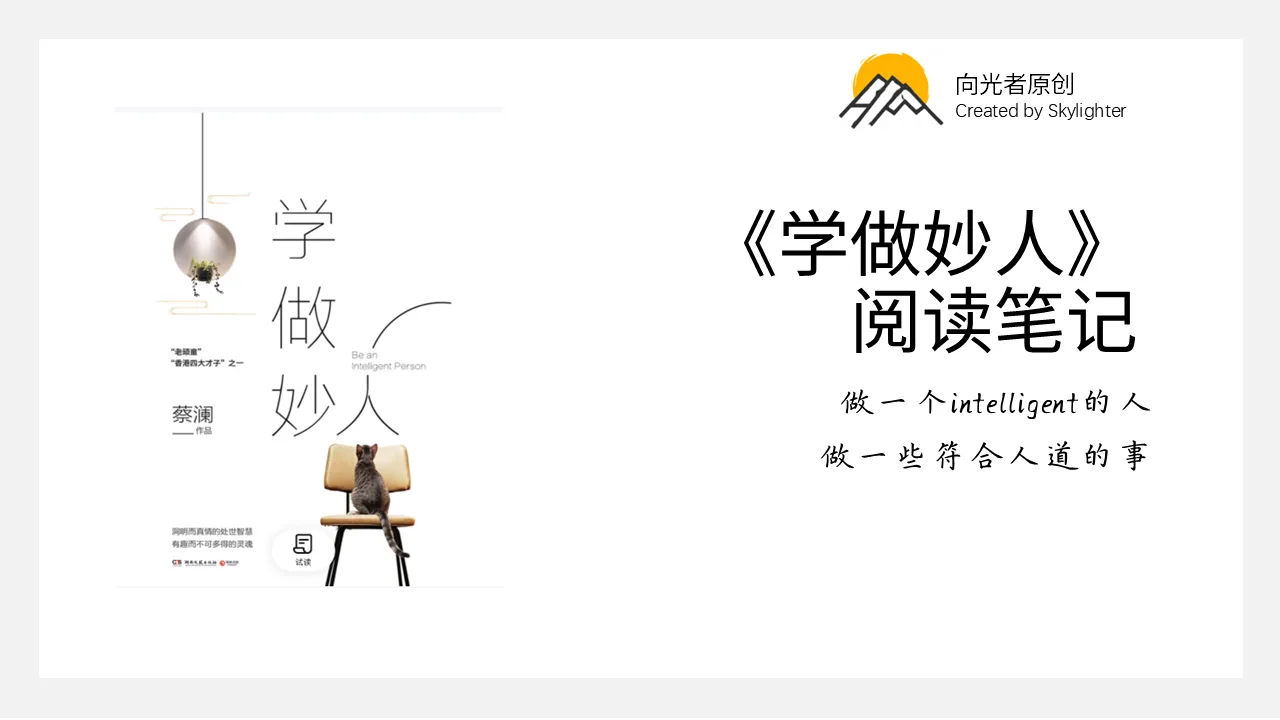在舆论的引导下,男女之间的对立达到了一个新高度。当大部分人都对这些事情耿耿于怀,甚至有一些“不支持(我的立场)就不是XX人”的观点出现了。新加坡资政李显龙曾经在公开场合提过新加坡人和中国人是不一样的,当新加坡的立场和中国的立场不同的时候,很多中国人不理解“既然同文同宗同种,同言同语,那么你们为什么不同意”,甚至会骂“你们忘本”。的确,有些诡辩者就愿意给人贴标签。你站在中立的角度,他说你“理中客”,你发出了观点,他说你“偏袒人”。对于这样的事情,有一段时间我曾百思不得其解,为什么会这样?
然而,后来我想通了,这个过程无非是建立在群体认同基础之上,利用语言暴力来建构身份政治,利用思维陷阱实现不良目的。
集体化固然好,但是我的人生不是别人的人生。正如新加坡歌曲《小人物的心声》一样,我的时间由我控制,未来日子一样会充实。
如果你度过《世说新语》,以及魏晋南北朝的历史,就会发现何曾、王衍、王戎、潘岳等这大批风流名士、乌衣子弟,其实猥琐龌龊得很,政治生涯和实际生活之卑鄙下流,与他们的漂亮谈吐适成对照。
一个人如果能够率真潇洒、轻松活泼,对于人生中的失落或不愉快遭遇处之坦然,若无其事。不抱怨外在环境的变化。蔡澜先生在金庸先生的眼中是一个非常有趣的人。蔡先生的知识面丰富,涉猎很广,所以底蕴厚重,但有很多面,让人猜不透他到底是什么样的人。蔡先生身上一种当代济公的影子特别令人向往之。
人生是有时间限制的,尽管我也想用斜杠青年的方式来圆融掉躺平和内卷,然而毕竟人生经历不足,周围没有人带着我,所以只能通过读书这个“无根之水”来逐渐滋养我自己。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就是如何分配我的人生。
今年的阅读量的确超过了往年,这让我有机会比以往多学了一些东西。蔡澜先生在这里亮明了一个观点:“等到你能确定什么时候是‘最’好,生命也已经是‘最’老”。
《水浒传》中李逵的咏史诗中提过一句“文无第一,武无第二”。所以很多人都要争夺第一,最好,最佳,不想做最差,最烂……在我所接受教育,并逐渐形成我现在思维的过程中,一个“最”就是第一,top1。仿佛做不到这个位置就没有办法活下去。其实,这个想法的适用范围就是当自己的内在实力已经超强的情况下,要把一个行业卷起来的结果。李光耀当年治理新加坡所用的其中一个手段就是这样。然而,刻意追求“最”,就进入了陷阱。“最”,背后有评价标准,谁定的评价标准?
罗振宇曾经说:我要做我自己出的卷子。可见那时的他已经看到了,答别人的答卷永远答不完。
答卷,就是一种做学问的过程。任何人都不能在所有领域都精通,换句话说,我现在对某些人动不动以“科学家”、“军事家”、“歌唱家”、“艺术家”的称号产生了麻木感。就拿我们披着“知识分子”外衣的人来说,身上有一个坏毛病,就是学会一样东西,听到一个事件,就敢自称专家,大声疾呼“这题我会”。
有人学书法,碑帖没有临摹多少就敢自创字体。有人学画画,素描刚学完,写实写意都不知道就敢自创画派。更有些人,我看了这本书,又看了那本书。然后就去发表文章,今天攻击这个人,明天批评那个人。懂得一点皮毛,即可引用。
自吹自擂的人,一定自信心不强。
——蔡澜
我们都是从农民成长起来的,中国人与土地的关系很亲,所以当走到农民中间去,会感叹:你们会看月色、能预测天气、真是了不起。但是农民耸耸肩,没什么了不起的 。
我们不可能成为下一个李光耀,也没有必要成为下一个李光耀。我们自己做好自己就行。与其说新加坡有什么奇迹,不如说李光耀懂得一个词“学问”。所谓学问,学学问问,就学会了嘛。真正学会的人,却像农夫一样不出声,耸耸肩:没有什么了不起。
最怕你不愿去学,不肯去问。
写这个读书笔记,不在乎自己能够记住全部。谁也不能靠大脑把一生的话全都记下来。
蔡澜说:我只是写,每天写,不知道会不会。
这句话真好。
我只是学,每天学,不知道好不好
我只是做,每天做,不知道行不行
我只是写,每天写,不知道会不会
我只是背,每天背,不知道牢不牢
把每个东西掌握到前25%,就行了。人生潇洒,过得舒坦,真好。
无用,为大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