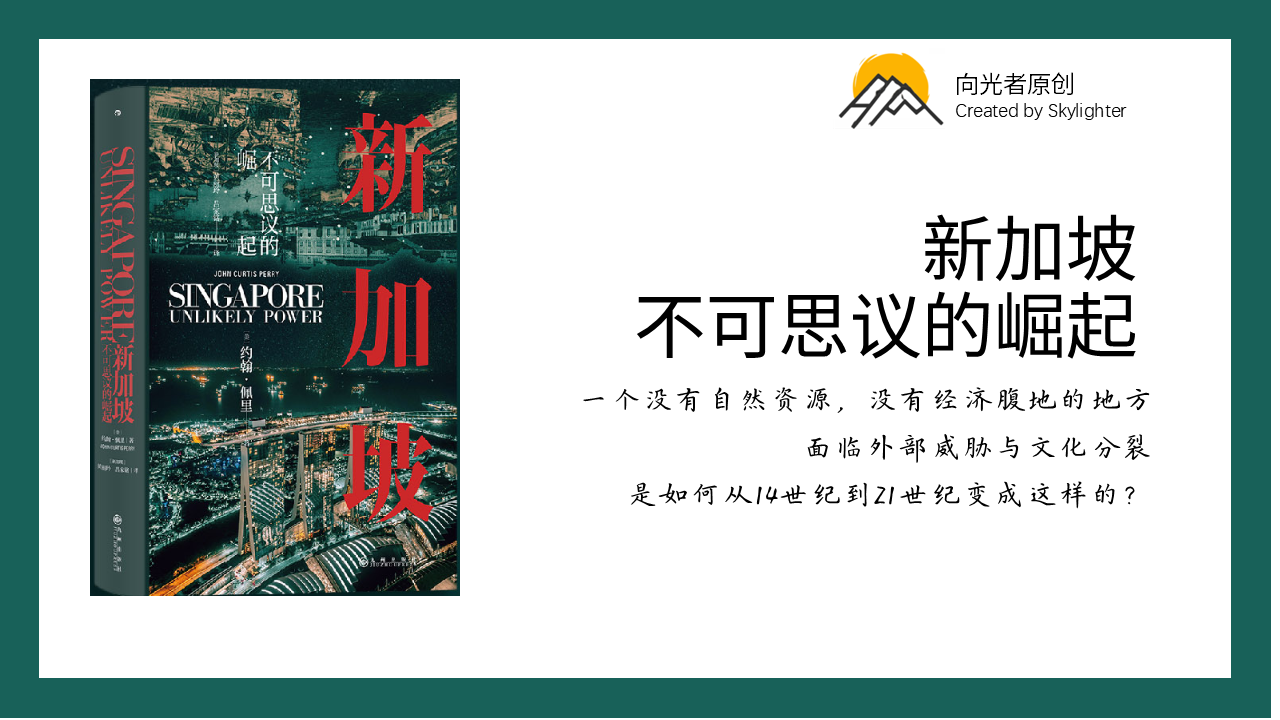上次我们的阅读笔记中说道。中国人在16世纪的时候就前往了“南洋”落地、生根,并且在没有渠道“入仕途”的前提下掌控了很多行业的命脉。郑和的七下西洋为中国人在东南亚的地位又贡献了力量。就在穆斯林文化和中国人交织的过程后,为什么以英国人为代表的欧洲势力前期没有控制,但后面却占有了东南亚呢?
所有的原因,就在于的欧洲人的一个特质:海上行动力极强。前往非洲的中国人也毕竟是极少数。但是欧洲人不同,当他们了解并掌握了中国造船技术之后,并不像郑和一样只在区域内行动。而打通了欧洲到中国、美洲的道路,使全球化拉开了它面纱下的那张容颜。
荷兰人一战成名
14世纪到17世纪,当明朝还在巩固政权时,欧洲文艺复兴的风潮使得全欧洲开开始了对世界的探索。当时,作为起源地的意大利,其威尼斯、热那亚和佛罗伦萨大量发展经济,培养人才,极大推动了葡萄牙人和西班牙人在大西洋的扩张。而中国的丝绸与瓷器、印度群岛的香料吸引着他们绕过非洲、南美洲,通过建立战略要地而设置贸易前哨,以稳固全球贸易。
比如葡萄牙人,在1511年的时候在马六甲的岸边设立了一个石头堡垒,命名为A Famosa(“著名的”),希望船只在这个堡垒下落锚,同样希望这个海上运输进一步加强这个堡垒的补给能力。然而,当地居民见状立刻搬离到柔佛、苏门答腊等地,使得马六甲再也没有回复荣光。更严重的是,这暴露了马六甲的军事弱点和葡萄牙人对当地的浅薄认知。
欧洲长途贸易中获益的荷兰人见状后,于1603年和葡萄牙人展开竞争,然而这种竞争却是我们中国人的耻辱。这一年,葡萄牙帆船“圣卡塔琳娜(Santa Catarina)”号载有荷兰东印度公司一半资金总量价值的中国货品从澳门出发。船上不仅有货物,而且还将中国的妇女和儿童也当做货物,作为奴隶或小妾出售给有意的买家。
2月25日早上,当荷兰船队发现这艘帆船时,通过整整一天的炮击击中了船帆,使得这艘载有800多人的船丧失动力。葡萄牙人最终交出船和货物,以换的荷兰人对乘员安全的保证。这一次冲突极大地打击了葡萄牙军事声望。不仅如此,雨果(Hugo Grotius)通过匿名写作的《海洋自由论》(Mare Liberum)为这次行为成功的洗白。也让葡萄牙人颜面扫地。
在当时,荷兰全民在争取独立和建立世界上第一个现代经济体的过程中,不断确立自己的政治身份。因此他们依托侵略性的海上力量和精明的商业头脑,抓住每一个商业机会,在1641年彻底赶走了葡萄牙人,在重建A Famosa的过程中增建了一个护城河网络。荷兰人精明就在当他发现这个前哨站无利可图的时候,果断放弃,并且寻找新加坡和其他岛屿作为替代。
终于,印尼群岛中的爪哇岛成为了荷兰人下一个觊觎对象。他们对Sunda Straits的控制胜过一切。在荷兰人的印象中,在印尼群岛或亚洲大陆上立足,就能够限制其他欧洲人在亚洲的发展空间。直到1824年,荷兰人不仅没有放弃,反而加紧对印尼群岛的控制。
嫉妒心的英国人
英国人对亚洲的注意力始于印度,对东南亚始终保有厌恶的心态:“热带丛林险恶,疾病与死亡高发,动物凶猛人也野蛮”。当柔佛苏丹向苏格兰船长Alexander Hamilton提议出售新加坡岛的时候居然被拒绝,这就可见一斑。
然而,英国人对香料和精美物品的来源有所了解后,意识到马六甲海峡是通向中国的最直接航道,对于日益增长进口中国茶叶的需求也让英国人思考。这个最重要的诱惑使英国人对东南亚一带的兴趣倍增。
既然要控制航道,根据地是必须要有的。1790年,英国皇家海军军官Francis Light从吉打州苏丹手中以6,000元/年的价格租借了槟城。槟城在海峡西部太远。除了槟城,还有一些地方在荷兰控制之下。19世纪早期的政治家George Canning说:“但凡商务上的合作,荷兰人总是给的太少,要的太多。”与此同时,英国人长期以来对荷兰有一种心不甘情不愿的崇拜。
躲避荷兰人终究不是办法,所以在1795年,英国从荷兰人手中夺取马六甲城,不惜付出代价炸毁了A Famosa。因为在英国人骨子里看来:只要统治了海域,才有安全感。此时,汇集印度、中国、东南亚和本国的大量产品在这里积攒起了英国的巨大利润。英国的钢铁工具和硬件、印度的棉花和鸦片、中国的瓷器和茶叶,马来亚的翠鸟羽毛、药品和热带硬木木材。
别看这么多,但是当新加坡开始出现在英国人的心中时,并不是很好的选择,直到一个人的出现,新加坡才开始出现了不一样的道路。
莱福士的初印象
走在新加坡核心区,你会发现很多以Raffles命名的地方。这个人的全名叫做Thomas Stamford Raffles。
1781年,莱福士出生在加勒比的海上,然而他父亲抛妻弃子,使得莱福士从小缺失父爱,然而母爱的持续,塑造了他自信、有野心、极其果断、热情和独立的性格。1795年,莱福士的父亲离世,作为在伦敦求学的家中独子,他只能辍学,前往东印度公司伦敦总部印度大楼里担任普通文员。虽然辍学,但是它凭借强大的求知欲和精力充沛的心态,在费尽心思照顾母亲和兄弟姐妹的同时,还热心帮助同事,有着积极向上的态度去时刻准备好学习。他经常提笔鏖战到深夜,将大量的信息压缩成简洁且有说服力的小论文。
1805年9月,上司派莱福士前往槟城殖民地,然而在英国殖民等级制度中,对于他这样一个没钱没地位的家庭背景的人很难融入当地的英国社群。但是,拥有社交才能与有影响力的英国人打交道,得到他们的资助和友谊。同时,他也花了不少时间研究自己感兴趣的与马来人有关的学术领域。更重要的是,马来语在他语言天赋的支持下比官方翻译人员更为娴熟。
通晓马来语是莱福士和马来社区建立关系的一笔宝贵财富。收集信息也是莱福士的巨大兴趣。在和马来人接触的过程中,它积极吸收马来文化艺术的各个领域:婚俗、葬礼、人们的工作方式、交易方式等等。他想象着建立一个横跨马来半岛和印尼半岛的马来族群国家,因为他相信马来人具有冒险精神和商业头脑。
因为相信,尽管同为英国人,但莱福士与他的英国上层看法截然不同。随着和马来社区的不断融合,它脑海中构建出了一个具有大跨度的马来世界,在地理上从马来半岛直到印尼最东段,在文化上将马来文化与英吉利文化平等对待,并在英国的良性引导下扩大影响范围,从而恢复马来族群昔日的荣耀。
不论莱福士做这些事情是出于真心,还是希望用另一种方式来维持英国的殖民统治,但是可以看到的是,莱福士开始行动了。他首先选择新加坡附近的廖内群岛作为初始据点,这个群岛是印度到中国的必经之路,也是与加里曼丹、苏拉威西岛和马鲁古群岛更近的地方,后者可以提供肉豆蔻、豆蔻皮、丁香等宝贵香料。其次,在1817年回国探亲时,他发表了一步关于爪哇历史的著作,阐述这个群岛的重要性。
然而,英国官方仍然没有把这个意见当回事,除了给他封以爵士的称号之外,收获到的另一个“礼物”是让他到苏门答腊岛上做一个明古鲁副总督。这个地方早就被荒废。也就是说,莱福士被进一步边缘化。很显然,这是背后的那些英国上层阶级所做的内部斗争。莱福士一气之下前往印度加尔各答,与印度总督求告自己状况后,总督起草一纸命令,建立新的海峡基地——新加坡。
走进新加坡国家博物馆,有一段史料曾经说:“莱福士和威廉·法夸尔共同缔造了新加坡”。这与莱福士后来接受采访所说的内容大相径庭。孰是孰非已然不重要了。新加坡,这个远离台风侵扰,在方圆1000英里内最深的港口就这样成为了英国的驻扎地。
事实也如此,新加坡古老的贸易传统,太平洋与印度洋的绝佳联结地,相比起其他海峡而言,这里提供了最直接的航道。
来去匆匆的莱福士
要想在新加坡建立据点,有三个问题是必须要解决的。一是在新加坡岛建立据点能否承受的住马来人的反对,二是如何化解伦敦方面不情不愿的态度,三是如何抵挡来自荷兰的强烈反抗。要知道,新加坡规模狭小、缺乏防御工事、距离本区域行政中心较远。
作为一个决策者和思想家,莱福士不断思考这个地方的发展,比如国家战略、反思过去与展望未来等等。他先把新加坡历史进行重构,描述为海上帝国的中心。给了新加坡历史的合法性和尊严,此外,保留了港口的名字为Singapura,虽然之后经过了Singapoor和Singapore。
第一,马来人认为莱福士和当地王公之间的协议出卖了他们的领土主权和贸易圈。
第二,荷兰人向英国告状,说莱福士代表的东印度集团与马来人签订协议无效。而总督撤销了给莱福士的批准。而远在伦敦的那些王公大臣,则对此进行无声的反对。
第三,莱福士认为荷兰人是“罪大恶极的敌人”,荷兰人为了自己的商业利益没有管住“无法无天的华人、阿拉伯人和美国人”。然而,英国本土却希望荷兰实力增强以对抗老牌劲敌法国。
就这三点让莱福士焦头烂额,尽管他一直保持英国精神“如果商业给我们的祖国(指英国)带来财富,那么文学和慈善主义的精神将教会我们最高尚地分配和治理财富。这会使英国成为世界上最强大的力量。”,然而不断增加的人口数量使得莱福士无能为力管理这里,且在此期间,他的第一任夫人和5个孩子中的四个因为热带疾病而去世。这给他严重的打击,
屋漏偏逢连夜雨,1824年,刚刚回到英国的莱福士接到雇主东印度公司的指控,声称莱福士拖欠东印度公司的财产,没有多久,1826年7月5日,莱福士因脑瘤压迫神经,在46岁之前在家中楼梯口去世。
莱福士的一生给我们启发,就是做事不要太贪婪高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