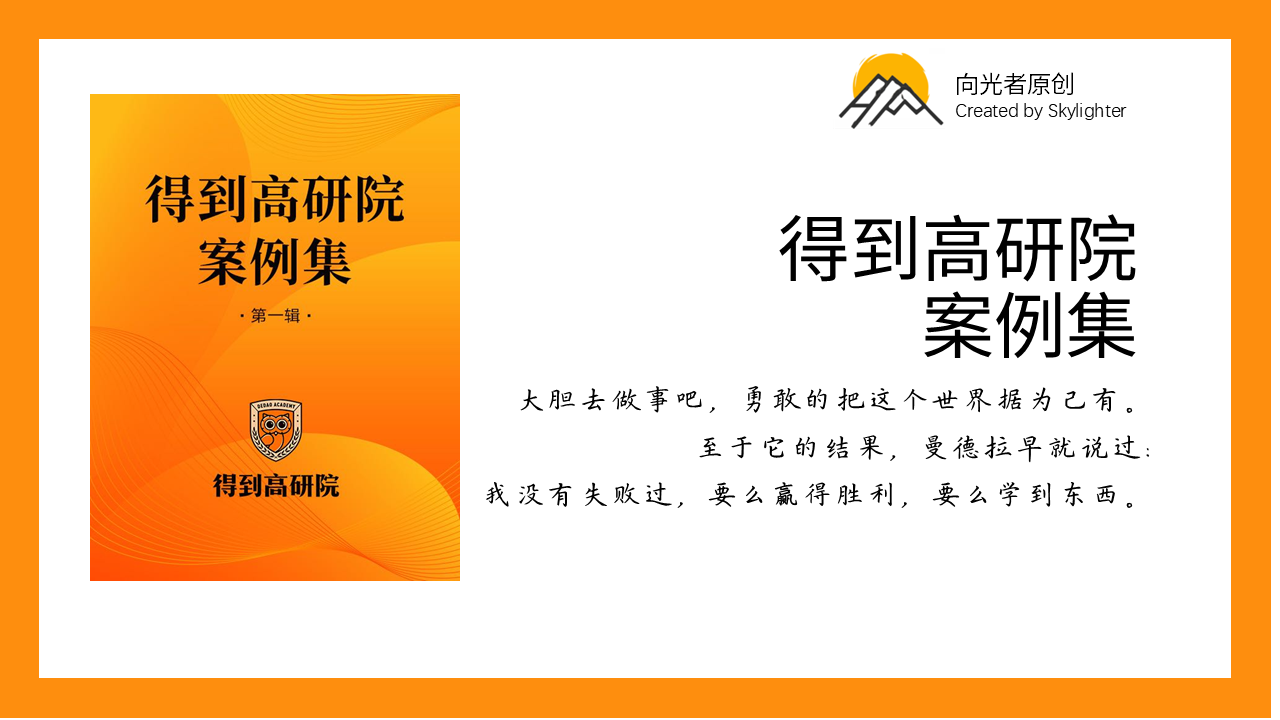神舟飞船,重8吨,总长8米,13个分系统,52台不同推力的发动机,电缆总长度超过30公里,600余台设备,10多万个元器件。参与研制单位超过1000家。
航天飞机零件更多,250万个。
对于复杂系统的研制而言,可想而知压力之大。而比巨大压力更让我们害怕的是三个字:“没问题”。特别对于复杂系统,但凡“没问题”才是最大的问题。
没问题,不是真的搞定了,而是意味着我们陷入了一种“不知道自己不知道”的境地,这才是最危险的。
这里的问题,不仅仅是故障,更多的是“路径依赖”所导致的认知盲区。一件事完全在认知范围之内,但是就是看不到这样的问题。
阿波罗1号飞船就是因为对纯氧方案的潜在威胁缺乏认识,导致三位宇航员在一次地面模拟实验装置失火而离开人世。纯氧环境下,很多本来不易燃的东西都变得易燃了。此外,舱门设计也因为着火后在飞船内部形成负压,90秒内是绝对没办法从外面打开。
因此,一名合格的航天工程师,就必须要有这样的一种能力。
工程师理念1:阻碍你前进的不是大山,而是“我知道”。所以,永远要假设“不知道自己不知道”,绝不轻易相信“没问题”。
只有这样,才有可能从这种状态进步到“知道自己不知道”。从“以为没问题”到“知道有问题”再到“解决真问题”。相反,一句“我知道”,就错过了对某项知识的了解机会。
突破认知边界的第一个意识:不管问题是什么,就必须排除它、解决它、掌控它。
做航空航天的人都知道,科研就是要探索未知。我们既不知道要去的地方那里有什么,也不知道那里没有什么。我们对那里几乎一无所知,也难以想象一无所知的东西。这就是我们面对的工作困境:常量太少,变量太多。
一切归于一个短语:巨大的不确定性。
为了抵达遥远的目标,我们需要在空间上、时间上、速度上,乃至认知上挑战极限。这就需要想象所有可能发生的情况,带上可能用到的一切东西。与魔术师不同,我们面对的系统太复杂,以现有的技术穷尽所有可能是无法实现的。具体说:我们无法提前预判哪里会出现风险,即“薛定谔的风险”。
工程师理念2:从没问题状态中把看不见的问题暴露出来,准确定位问题,找到方法把大问题转换为小问题。
暴露问题的方法根据阶段也有选择:对于飞行器设计而言,仿真就是暴露问题的方法;对于飞行器制造而言,测试就是暴露问题的方法。反复使用,也就是检验鲁棒性和可靠性。
比如说,一个电阻在西安就好的很,但是到了北京运行一周就出故障了。最终发现电阻中的空气有问题。这种微小的异常就是我们不能放过的部分。
发现问题很困难,但是一旦发现了,好像事情也不是很大。但是如果想永久、彻底解决问题,好像又不是那么容易?
所以,航天人有一个方法论:“归零法”。归零法不是从零开始,而是从经验开始,从新的认知边界出发。
归零法的本质,就是放大已经发现的任何微小异常,通过反复追问,不惜动员一切资源,找到问题背后的本质原因,从而彻底解决问题。
例如,我们人发胖了,金属腰带会剐蹭到卫星主发动机。这就必须要修理发动机。针对这个问题,我们还要修改工作规程,以后所有工程师都需要称体重、量腰围,进入现场要安检,工作服也改为松紧带的。
还要举一反三,研究其他环境:有没有类似的人机接口问题?操作高压器件时会不会放电?手上的油脂会不会产生危害?需要戴什么样的手套?头发会不会掉入精密仪器?这个问题一直追问下去,这个问题才算是彻底解决。
无论问题表现为什么具体现象,都要不停追问为什么,揪出现象背后的本质,最终彻底解决问题。
解决一个问题,突破一个边界。外面还有一个新边界。我们就是要在这个基础上不断前进一小步一小步。
正所谓:
——张拯宁
怕什么真理无穷,进一寸有一寸的欢喜!
管什么宇宙无限,成一次有一次的得到!